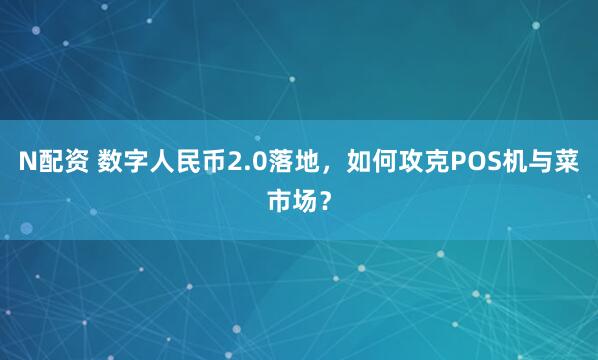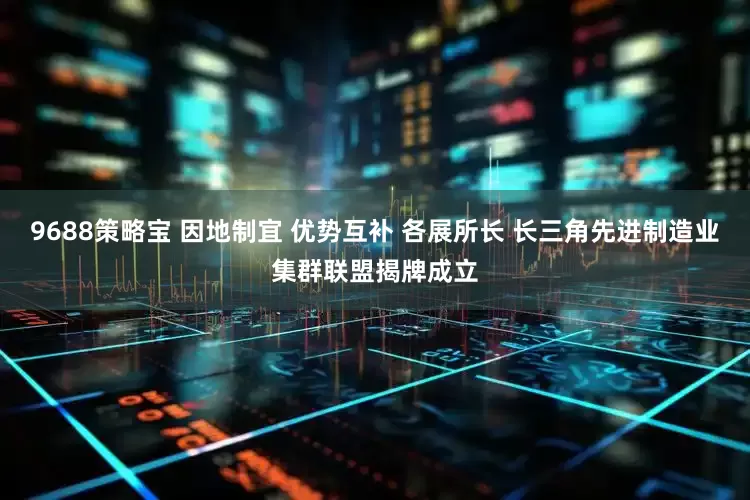在《关于崇高》一文中富余通,作家王小波讲述了一个故事——
上世纪七十年代,一条大河里发洪水,冲走了一根国有的电线杆。有位知青下水去追,木质电线杆没捞上来,人却淹死了。这位知青受到表彰,成了革命烈士。
王小波援引此事,想带出一个小小的困惑:我们的一条命,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?结果呢,因此困惑的人惨遭批判。
类似的困惑,如今又重新摆在我们面前。
2025年7月2日20时28分许,沪昆铁路上金属的撞击声划破夜空。一辆货物列车如失控的巨兽侵入下行正线,与K1373次旅客列车轰然相撞。当通报轻描淡写写下“机车前台车脱线,无人员伤亡”时,车厢内700多名乘客却正在37.9℃的夏夜中,坠入一场缓慢窒息的地狱——空调停转,通风断绝,汗水浸透的衣衫紧贴皮肤,孩童的哭声与老人急促的喘息在密闭空间里交织成绝望的交响。

根据媒体报道,其中一名乘客已经中暑,由列车员搀扶转移至其他车厢。
三小时后,一声玻璃碎裂的脆响刺破混沌。一位黑衣青年手中的安全锤砸向车窗,飞溅的玻璃碎片在灯光下如星辰散落。
在很多人看来,这不是破坏,而是一记刺向官僚惰性的锋利警钟。事后,一度传言黑衣青年被行拘,实际却是他接受了铁路公安的批评教育。不少网友认为,他不仅不应被批评,反而必须得到表扬。南都评论甚至以此作为标题,来呼应公共舆论。
针对网上争论,广铁官方发布了一份通报,归纳一下也就三层意思:
一是乘客闷不闷热,你们说了不算,是我们铁路说了算,我们说你不热就是不热,我们说你热你才热;二是不管你砸窗会拯救多少人,你说了不算,我们就认定你只要破窗就一定有人跳车,一切以我们的认定为准;三是你上了我们的车,就必须服从我们,你可以死在车上,但不可以反抗我们。
这份通报,既不讲法理富余通,也毫无人性,于是舆情再次升温。
铁路部门精心编织的安全网,在危机时刻暴露出惊人的空洞。当K1373化作“闷罐”,乘务人员坚守的指令竟是紧闭门窗——全然忘却《旅客列车空调失效应急处置办法》第九条明令:“空调失效超过20分钟不能恢复且列车不能维持运行时”,列车长应“视车内温度和旅客舒适度作出开门或开窗决定”。

同样被遗忘的还有《高速铁路动车组车辆故障应急处置办法》:停车超过20分钟即应开启应急通风系统或开门通风
交通部2018年第13号令,《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规则》明确规定,列车滞留后15分钟工作我员未有效处置疏散和通风问题的,旅客有权采取必要的自救措施,如破窗,使用应急设备等。
这些规章绝非尘封档案,而是铁路职工入职必考的生存法则。然而在三个小时的煎熬中,乘务员浑身湿透挡在窗前,反复拒绝乘客开窗请求的画面,将纸面规章化为无效的纸铠甲
当黑衣青年第三次沟通无果后挥起安全锤,他砸碎的不仅是玻璃,更是系统性的职业失能。
法律从不要求公民在危险中做沉默的殉道者。
依据《刑法》第二十一条与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二条,紧急避险的法定要件在黑衣青年的行动中得到完美诠释:
——现实危险:34℃密闭车厢内,多名乘客濒临中暑,儿童持续哭喊,成人自述“缺氧”;
——避险的不得已:乘客三次恳求乘务员开门通风被拒,无其他救济渠道;
——利益权衡:一扇车窗的价值远低于数百人的健康权乃至生命权;
——对象正确:损害对象为铁路方财产(车窗),而非危险制造者。
更关键的是,避险行为最终解除了全车危机——新鲜空气涌入后,乘务员立即接管现场:有人清理碎玻璃,有人守卫破窗防止跳车。
这场自救与官方处置形成戏剧性协作,印证了避险的正当性。
众多电影题材,从《雪国列车》到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,密闭飞驰的列车都载着一个巨大隐喻。K1373列车青年的砸窗举动,让本次事件超越一般事故,具备了极大的象征寓意。
K1373车厢曾是一座精密的权力金字塔:乘客在底层忍受蒸煮,乘务员在中层汗透衣背却不敢越雷池半步,决策者在千里之外的云端沉默。这种“安全服从”制造出荒诞的共谋:宁要形式安全,不要实质安全
黑衣青年的锤子落下时,他打破的是一种窒息性服从文化。当浑身湿透的乘务员象征性阻拦却未全力阻止,当玻璃碎裂后工作人员立即各司其职——这些细节揭露了更深层的真相:基层人员同样渴望打破僵局,却困于体制镣铐。青年的勇气成为所有人的出口,让机械服从让位于生命至上的实践理性。
铁路公安对砸窗者“批评教育”的处理,暴露了权责关系的根本错位。当广铁怀化公安处轻描淡写释放青年时,他们回避了核心问题:真正需要“教育”的是那些将应急预案遗忘在考场的乘务团队,是那些在空调失效后仍机械执行封闭指令的车长,是制定规则却未确保规则落地的管理者。
法律从不苛求公民做危险的殉道者。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二条的紧急避险条款,正是对“砸窗权”最庄严的背书——当制度防护失效时,公民自救权是最后的盾牌。
我们都有可能是K1373的乘客,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,你是等待被高温驯服的顺从者,还是成为打破窒息之窗的勇者?㳒
融胜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